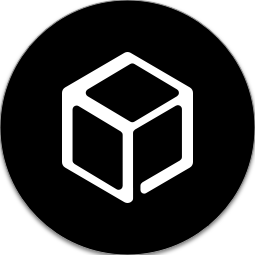茶渍和冰裂纹
旧书页边缘洇着深浅不一的茶渍,像某种古老的地形图,手指抚过那些凹凸的纹路时,总能触到某个潮湿的午后——雨滴在窗前敲打莫尔斯密码,你坐在藤椅里读济慈,玻璃杯里的茉莉花苞正缓慢地枯萎。
阁楼铁皮箱里锁着祖母的羊毛披肩,樟脑丸气味与霉斑在织物经纬间拉锯,却仍有零星的铃兰香从针脚渗出。这让我想起她总把栀子花别在第二颗盘扣,花瓣边缘的锈色沿着衣褶蔓延,最终在领口凝成永夜形状的污渍。
老邮局墙角的铸铁信箱,投信口结着蛛网。那些未被取走的信笺正在黑暗中发酵,钢笔水在岁月里晕成蓝紫色的静脉,有时深夜经过,会听见薄脆的信封在铁皮内壁轻轻翻动,像一群困在琥珀里的飞蛾在扑打翅膀。
九月银杏叶飘落的速度,与童年旋转木马下沉的速度惊人相似。金箔般的叶片贴在柏油路面,被车轮反复拓印,逐渐变成半透明的标本。某个相似的黄昏,我曾蹲在游乐场边看彩色灯泡逐一亮起,掌心攥着融化的草莓冰棍,糖浆沿着手腕爬进袖口,至今仍能在毛衣袖子上找到凝固的甜味。
本文是原创文章,采用CC BY-NC-SA 4.0协议,完整转载请注明来自解揽者备忘录